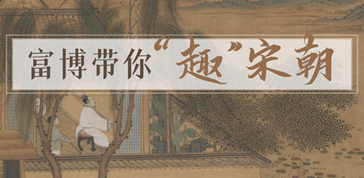宋人在读书、闲居、烹茶、雅集、欣赏音乐、宴客的时候,都会烧一炉合香,氤氲一室。深谙香道的黄庭坚还归自言:“天资喜文事,如我有香癖。”可见香在文人心目中的重要性。如果抽掉了焚香,宋朝文人一定会认为他们的生活将失去了数不尽的清趣。
在南宋刘松年(传)的《山馆读书图》与《秋窗读易图》上,我们看到,读书人的案头都放置着小巧的香炉,那是因为宋人读书时有焚香的习惯。许多宋诗也描绘了这样的文人习惯,如陈必复的《山中冬至》:“读易烧香自闭门,懒于世故苦纷纷。”戴复古的《赣州上清道院呈姚雪蓬》:“短墙不碍远山青,无事烧香读道经。”陈宓的《和喻景山》:“而今已办还山计,对卷烧香爱日长。”
今天我们能够看到两幅宋人的《听琴图》,一幅传为宋徽宗赵佶所绘,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;另一幅传为刘松年所绘,现为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。两幅《听琴图》都画出了一张香几,香几上放着一只香炉,显示宋人在欣赏音乐时,也会焚香渲染气氛,正所谓“约客有时同把酒,横琴无事自烧香”。
而宋徽宗的另一幅作品《文会图》,画的是文人雅集、宴会的图景,图中绘有一块大石桌,上面放了一只黑漆古琴,以及一个青铜香炉。
传为刘松年所绘的四幅《十八学士图》,其中一幅的主题就是“品香”。
传为李公麟的《西园雅集图卷》,描绘了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秦观等名士的一次雅集,图卷中苏轼正在作画,画案上也放了一个精致的白瓷香炉,“炉烟方袅,草木自馨,人间清旷之乐,不过于此”。烧香是宋朝文人宴客雅集时必不可少的点缀,宋人说:“今日燕集,往往焚香以娱客。”这叫作“燕集焚香”。
焚香作为一种文人雅道,是宋人发展起来的。当然中国人用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,不过宋人之前,焚香只是皇室、贵族的时尚,或者表现为佛堂供香。由于香被认为有“感格鬼神”之功效,而且寺院一直是财力雄厚的机构,佛堂供香通常非常华贵。传为李公麟绘画的《维摩演教图卷》上,就画有一张造型华丽的香几,上面放置的香炉是莲花座狻猊出香。这类华美的香炉,可见于北宋徐兢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的记载:“狻猊出香亦翡色也,上为蹲兽,下有仰莲以承之,诸器唯此物最精绝。”
宋人的焚香,你要说它平民化,它又讲究到极致,连“气尤酷烈”的名贵番舶沉香都被士大夫评为“不复风味,惟可入药,南人贱之”,剥夺了其作为焚香品的资格。但你要说它太讲究,它又有十分平民化的一面,寒门子弟用荔枝壳调制出来的合香,也被誉为“有自然之香”,优雅的焚香之道,始终向寒士敞开一扇门扉。这也是宋代香道兴盛的一大原因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