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2年11月,我顶父亲的职,进了杭州公交大修厂。
进厂前,我做好了准备,什么岗位苦,我就干什么。当时杭州的公交车都是公交大修厂自己造、自己修。我进了机修车间,当了一名钳工。
机修车间噪音大、油污重,年轻人要么没干几天就跑掉了,要么“老三老四”,不把老师傅放在眼里。
我每天勤勤恳恳,忙完了分内活,看哪个师傅在忙,我就去帮忙。每个老师傅都有自己的绝招,我就跟着学。

在公交大修厂做钳工的孔胜东。
早上我第一个到车间,烧开水、搞卫生;晚上我最后一个走,把师傅们的洗脸打好。没活干的时候,我就闷头练钳工的基本功:锯割、锉削、钻孔……老师傅们看我工作认真踏实,都愿意带我。
这时候,社会上很多人“下海”。我有同学开公司,喊我去帮忙——“单位给你多少(工资),我翻倍。”我又拒绝了,我热爱我的机修钳工岗位,既然选择了修车,我就要把这份工作干好。
我在车上多提醒几句,有的乘客就说,“这个男人家噶背的”
没想到时代在进步,有一天我们不用自己生产公交车了,而是向外面购买。大修厂的工人要往一线分流。当时最缺人手的岗位是乘务员,一个月休息不到一天。有的女同志哭哭啼啼不肯去。我主动申请转岗。
我说有困难,年轻人就要站出来。直到我打第三回报告,领导看我这么坚决,才同意。
1993年1月,我成为28路公交车的乘务员。我想杭州是旅游城市,来的外地游客多,到了每个站点,报站时我就延伸开去,作点简单介绍。比如体育馆到了,“下一站市体育馆,浙江日报社、杭州日报社、中国丝绸城。”到了年底,杭州的老百姓要订报纸,问杭报在哪里?我说体育馆下车往西走。外地游客问,我要买丝绸怎么办?“下车斜过去就是中国丝绸城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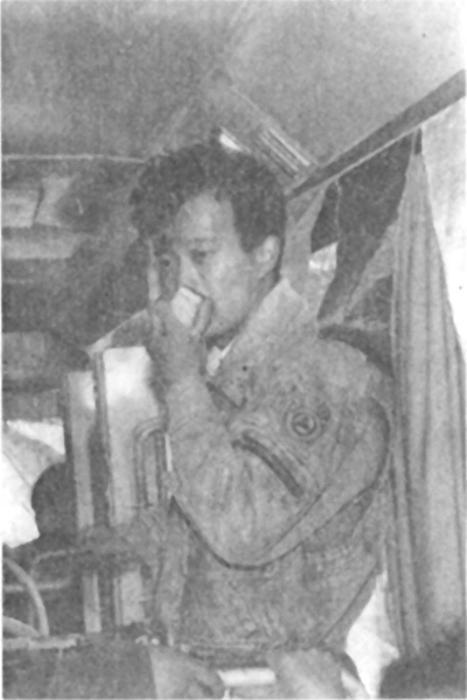
1995年,当公交乘务员时的孔胜东。(资料图)
再比如武林广场,“下一站武林广场,浙江展览馆、延安路、银泰大厦、杭州大厦,要转地铁1号线、3号线的乘客,请准备从后门下车,下车时请注意,包、手机、IC卡、月票请不要忘记,谢谢配合。”
乘务员的座位前有个柜子。上下班高峰,我就抱起没座位的孩子在柜子上坐一坐,或者让年纪大的人往柜子上靠一靠。乘务员大都是女的,男的就我一个,我在车上多讲几句、多提醒几句,有的乘客就说,“这个男人家噶背的。”


